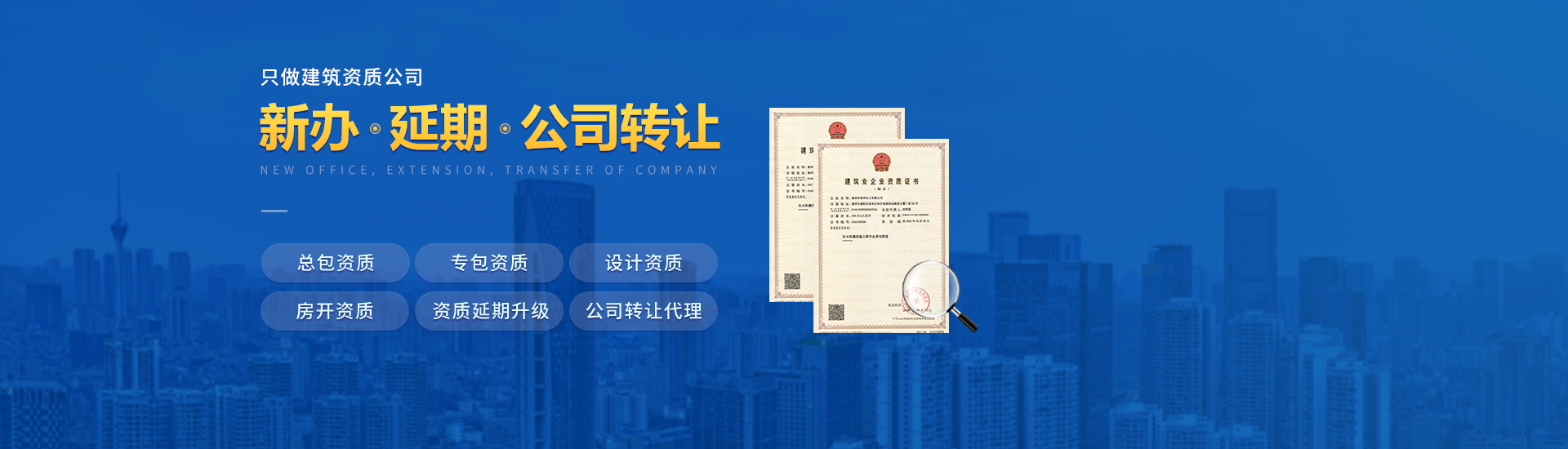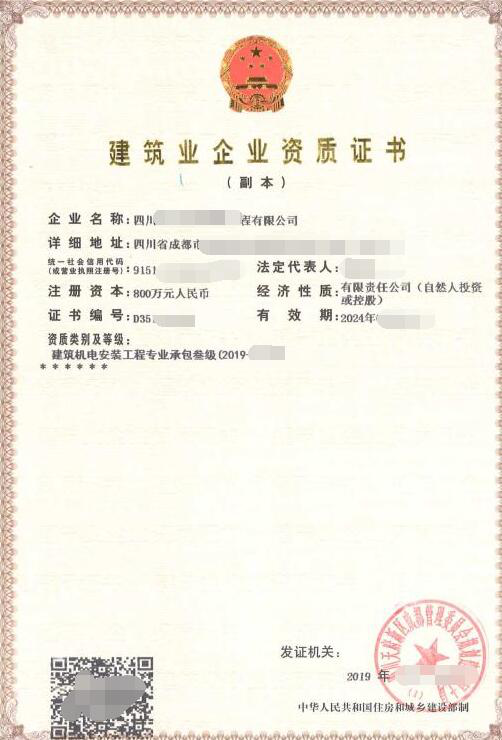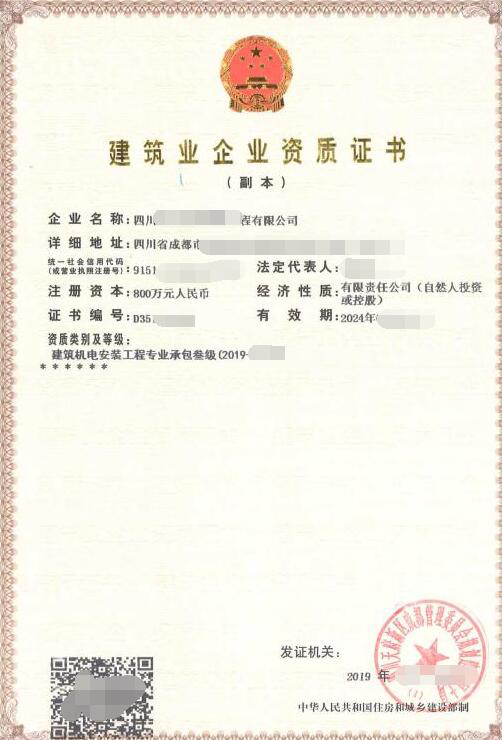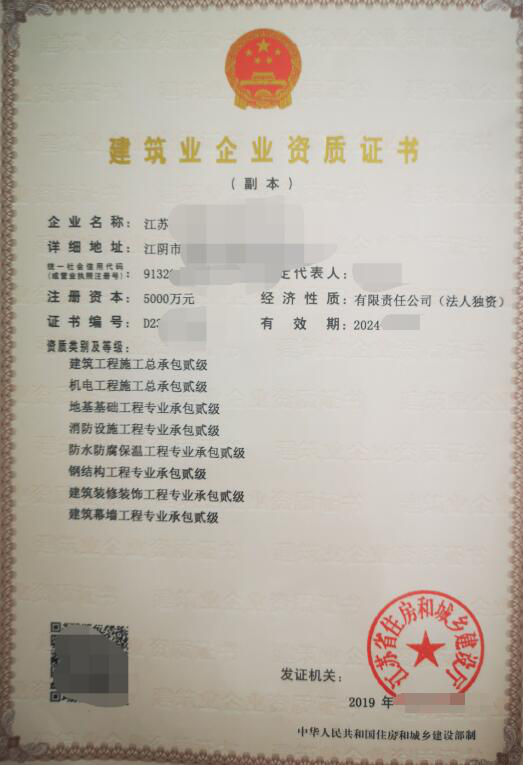“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當大唐浪漫詩仙李白揮灑樂府《蜀道難》1200多年之后,在古蜀國故地成都平原一個叫“三星堆”的地方,忽然有了驚天發現:一大批駭世驚俗的青銅、金銀、玉石、象牙等文物噴薄而出,讓此前縹緲流傳于神話、只言片語于史籍之中的古蜀國,漸漸撩開了神秘的面紗。
“三星伴月堆”——在傳說與史實之間
三星堆,原本就是四川省成都市偏北的平原上三個起伏相連的土堆,具體位置是現在廣漢市南興鎮三星村。三堆土北隔馬牧河與月亮灣臺地相望,清代以來雅稱“三星伴月堆”。直到1929年,當地農民燕道誠一鋤頭下去,刨到了直徑半米的大石璧,接著發現了400多件玉石器物,從而,一個被稱為“20世紀人類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的古蜀國文明遺址揭開了帷幕。這時,人們才發現,那三個土堆其實并非風雨的雕塑,而是夏商時期古人夯筑城墻的劫余。殘垣由于數千年的自然力量和人類活動,漸漸剝落成一條起伏錯落的土埂。從此,“三星堆文化”也以神秘、凌厲的姿態迅速切入大眾的視野。
從1929年開始陸續挖掘,三星堆文物不斷涌現。尤其是1986年一號、二號器物坑(祭祀坑)出土了6600多件品類豐繁、璀璨精奇的文物,震驚了世界。三星堆文物深寓獨特的文化信仰與價值觀念,具有深邃的文化內涵和鮮明的藝術特色,在世界上也屬于最具歷史科學文化藝術價值、最富觀賞性的文物品類之一。在這些曠世神品中,有以神秘詭譎的青銅雕像、銅神壇為代表的青銅器群,有以流光溢彩的金杖、金面罩為代表的金器群,還有以“祭山圖”玉璋、神樹紋玉琮為代表的玉石器群等,令人目不暇接。
“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三星堆從各個側面向人們展現出一個夢想充溢、氣象萬千的古蜀文明。考古學上的“三星堆文化”是指年代為公元前2100~公元前600年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及東部的峽江地區的一支考古文化,距今約4100年到2600年前,相當于黃河流域的夏、商和周初,其發展程度遠遠超出人們對于古代四川的認知。
一直以來,上古的四川地區都被看作是幾無文化可言的戎狄之域,有信史的年代已經到了戰國時代,即秦滅巴蜀的公元前316年(距今2300年前),史書記載巴蜀人民擺脫野蠻、愛好文雅也是從漢景帝派文翁入蜀教化才開始的。《說文解字》《水經注》《蜀王本紀》等文獻中都有關于古蜀國神話的零星記載,這些書有的已經亡佚,只有佚文還保留在其他書的引文里面。根據這些零星的古史傳說和文獻記載,在秦帝國將四川盆地納入其版圖之前,盆地西部平原上曾有一個歷經夏、商、周三代的古老國家——“蜀”,它創造過非常繁盛的文明,甚至殷墟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與“蜀”的往來。一直到李白生活在四川的唐朝,古蜀國歷史仍存在于神話和傳說中。傳說蜀人的始祖“蠶叢”及其民眾居住在川西高原上的岷山地區,被稱為“蜀山氏”,其后另一位首領“柏灌”帶領部分人東進成都平原,又經過“魚鳧”“杜宇”“開明”三個時代,最終于公元前316年被秦所滅。三星堆文化雖然沒有文字自證,但它的位置、年代、文化特征和內涵,都與傳說中的古蜀國極其吻合。所以,目前學術界一致認為,三星堆正是古蜀國的遺址,并且應是該國的中心都邑。
“堆列三星、古蜀之眼”——古蜀文化新家園
在三星堆遺址以北不遠處,有一條鴨子河,注入長江的支流沱江。河畔有著成片的濕地森林,遠眺可見連綿的雪山。在大地自然景觀的背景映襯下,三個連續的現代堆體建筑神秘而恢弘,這就是以“堆列三星、古蜀之眼”為核心設計理念的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文物寶貝們的新家園。
其實,早在1997年10月,當地政府為了收藏、保護出土文物和展示、研究三星堆文化,就在遺址的東北角建成了三星堆博物館,成為幾千件精彩文物安穩的家園和華美的舞臺。該館曾獲得“全國首屆城市紀念性建筑獎”“建國60周年建筑設計大獎”等眾多獎項,只是隨著考古勘探和重點發掘的不斷深入,只有兩個展館的老館已無法容納新文物的展示,博物館新館的建設計劃提上日程。
2020年10月10日,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和游客中心(新館)概念設計方案面向全球開啟征集,當時有來自國內外的57家設計公司及設計團隊報名。經過激烈角逐,由中國建筑西南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劉藝任總設計師的原創設計作品——“堆列三星,古蜀之眼”在眾多方案中脫穎而出,成功中選。2022年3月29日,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建設項目正式開工,由中國建筑第八工程局施工。2023年7月28日,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在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開幕當天正式開放,從項目立項、破土到竣工,只用了485天,再次驚艷了世界。
三星堆博物館新館的主體是三個連綿起伏的覆土堆體建筑,是對古蜀王國三個堆狀遺址文脈的呼應。而堆體建筑的幾何曲面源自老館二號館。作為遺址公園中軸線盡端的制高點,二號老館是三星堆著名的歷史地標,是前輩建筑大師鄭國英先生的代表作品。二號老館經典的螺旋曲線外墻,延展成為新館外形和內部空間曲線。堆體建筑屋頂采用斜坡覆土,朝著北側河岸方向緩緩下降、融入河堤,與大地渾然一體。三個堆體建筑的平面夾角呈現嚴謹的幾何圖形,生成獨特的形體韻律,寓意“堆列三星”。
“古蜀之眼”是指堆形建筑外立面兩個巨大的玻璃窗設計,這兩個玻璃窗就像三星堆青銅面具中的眼睛一樣,是視線交流的核心。人們在建筑的內部可以眺望到三星堆遺址園區,也能看到遠處的古城遺址,可以進行一場無聲的、穿越歷史的對話。
三星堆博物館中庭的“時空螺旋”是館內參觀動線的樞紐,360度環繞的坡道連接新館地上地下主要的樓層。三星堆二號老館標志性的圓形中庭朝向天空,象征“天眼”,代表著對天的崇拜,而新館則創造了向著地心旋轉的“地眼”,代表對大地的追尋,螺旋坡道盤旋而下,最終抵達建筑的最低點——地下負10米位置的圓形地坑。地坑的最深處,三束激光投影從圓孔中射出,在30米上方的天棚投出變幻的三星堆影像,寓意來自遠古的文明之光。“天眼”與“地眼”是對天地關系的闡釋,上天入地,連接起新館和老館,串聯起古今,也串聯起一個地域的文脈。
“王者之器”與“天山之祭”——古蜀王國猜想
古蜀國的歷史雖然因缺乏記載而“茫然”,但是,三星堆橫空出世的文物讓世人得以一窺古蜀國先民獨特的生存意象與瑰麗奇幻的精神世界,嘆服這個上古族群非凡的藝術想象力與驚人的創造力,也讓世人對古蜀王國的猜想有了實物依據。
在三星堆博物館一樓“巍然王都”展覽單元,展出一條長142厘米、直徑2.3厘米、重約500克的金杖,金皮原本包卷在木棒外面,出土時木棒已碳化成渣。金杖一端有圖案,上刻兩個頭戴五齒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墜的人頭像,還有鳥、魚、箭的圖案組合。學者推測,金杖可能與傳說中的“魚鳧時代”有關,金杖集神權、王權于一體,是政教合一體制下的“王者之器”。
戴金面罩的青銅人頭像是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57件青銅人頭像只有4件戴了金面罩。戴面罩的人頭像金光熠熠、尊嚴高貴、氣度非凡。學者推測,如果說金杖象征王權及神權,代表統治權威,那么金面罩施于極少數銅人頭像,則應是象征古蜀國的顯貴。從這個意義上說,金面罩在古蜀文化中是神圣、尊貴、權威的代表。以金飾面,彰顯神權與王權象征者容貌的神圣感、權威感。金箔薄如蟬翼,也表明當時捶打工藝高超,獨特的紋飾制作和粘貼方法更是在上古時期獨樹一幟。其他如虎形、璋形、魚形等金箔也都價值連城,在金器數量極為稀少的商周時期,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卻出土了金器65件(不含殘片、殘屑),總重約850克,對研究我國早期黃金制品意義重大。
祭山玉璋出土于三星堆二號祭祀坑,也是三星堆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玉璋所刻圖案構圖風格奇詭精麗,其中有云遮霧罩、層巒疊嶂的高山,有或站立或跪坐、神情莊重的人物,有冉冉升起的太陽,還有從天而降、觸于山腰上兩只神秘巨手等意象,合構成一幅充滿想象力的具有奇幻神圣色彩的畫面,其既有對人間社會、自然萬象的概括刻畫,又有對信仰世界的含蓄表達,內涵復雜而豐富。從玉璋刻繪圖像分析,大體可以推測該圖像應是隆重祭祀場面的寫照。但玉璋的圖案還有許多未解之謎,比如下層跪著的人和上層站著的人是什么關系,是否表示人間與神界?人物不同的姿態是否表意祭祀的儀式流程?圖像中懸空的不規則幾何圖形又是表現什么?可以說,三星堆文物的神秘性在這件玉璋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三星堆一號、二號祭祀坑共出土玉璋57件,大致分為三類:一類為邊璋,斜邊平口,略呈平行四邊形;一類為牙璋,呈長條狀,該類器物在陜西神木石峁龍山文化、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均有發現,但以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牙璋數量最多,制作最為精美;一類為魚形璋,璋的“射”部酷似魚的身體,“射”端呈叉口刃狀,宛如微張的魚嘴。魚形璋是蜀地特有的器型,目前僅見于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
三星堆典型的玉石文物還有玉璧、玉琮、玉斤、玉刀等,兩個祭祀坑出土的眾多玉石器足以證明,至遲在商代,古蜀人已有了較為完備的宗教禮儀制度,反映出古蜀國已具有相當強盛的綜合國力,而與之相適應的宗教禮儀制度已臻于完善。《周禮》記載的“六器”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琥、玉璋、玉璜,古代祭祀天地四方,即以璧禮天、以琮禮地、以圭禮東方、以琥禮西方、以璋禮南方、以璜禮北方。古人以玉作“六器”,玉之用,天地四方,無所不包。玉器作為通天、通神之禮器,在古人心目之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石器中禮器的數量最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蜀國的政治宗教文化。其中如璧、璋等都是古代祭儀中最為重要的禮器,璧以禮天、璋以祭山,“天山之祭”是古蜀人通靈、通神、通天的宗教祭祀禮儀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