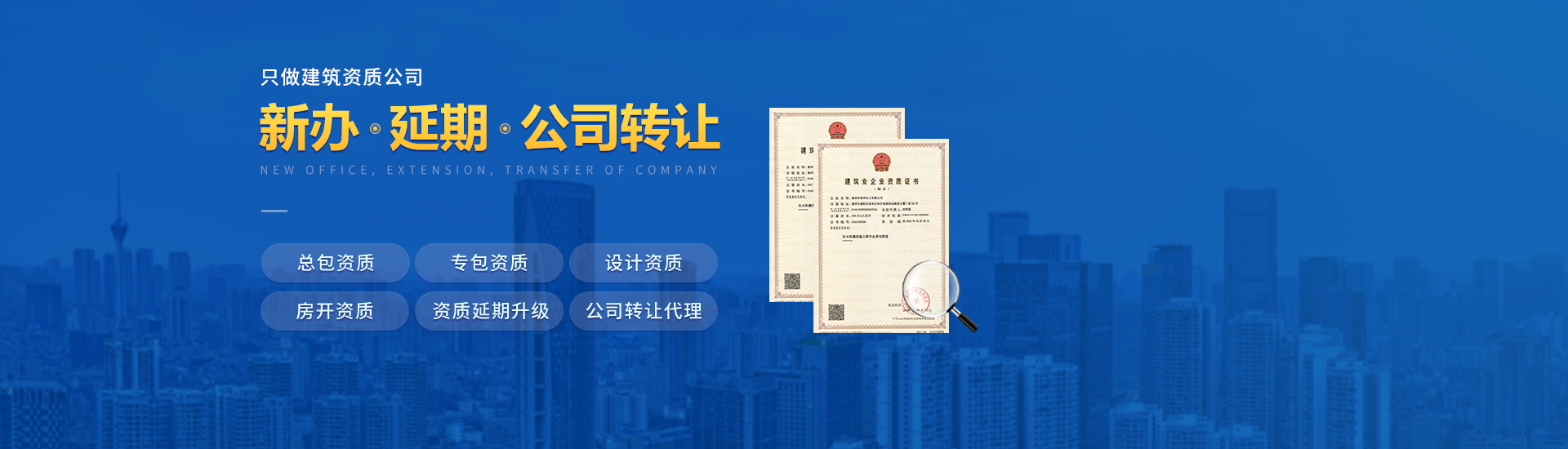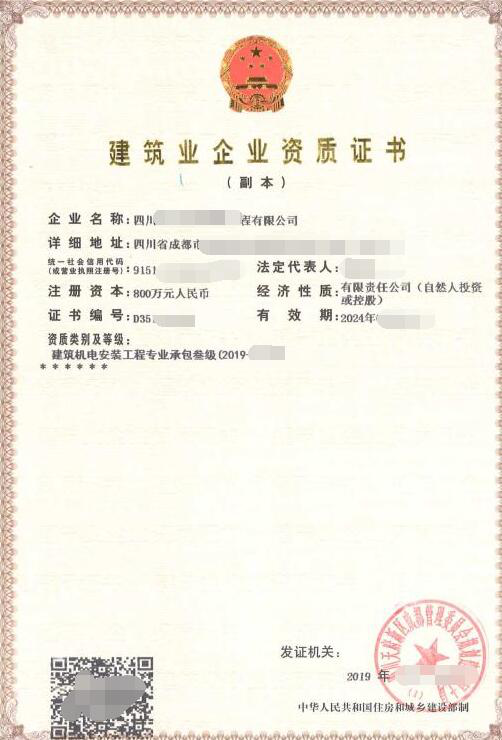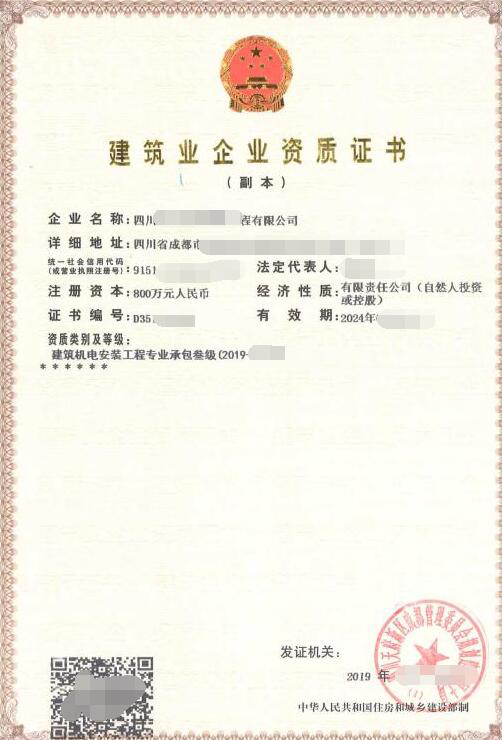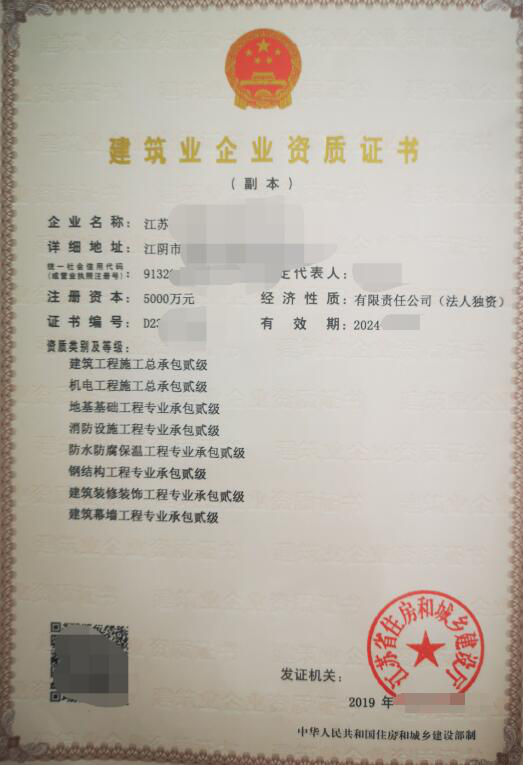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在施工過程中意外現(xiàn)世,旋即以“20世紀最偉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而震動寰宇。這座西漢初年長沙國丞相轪侯利蒼家一家三口的墓葬,不僅以跨越2000年的不腐女尸和流光溢彩的漆器帛畫驚艷世人,更激活了長沙城的一段遠古記憶——轪侯家族的煙火日常、少年將軍的戎馬豪情,以及辛追夫人對永生的極致想象。它背后不僅是一個逝去的家族,更是一個耀眼的時代,其中折疊的文明幾乎涵蓋了西漢以前整個中國的歷史。
錦繡漆器——辛追奢華的日常
辛追夫人所在的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千余件隨葬品,集中陳設于井槨內(nèi)的四個邊箱。它們就像四個房間,是對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擬,展現(xiàn)出轪侯家精致的日常。如今在湖南博物院的三樓展廳,這些精心挑選和擺放的隨葬品仍保持著精心的陳設布局,隔著2000多年的時光,這些還留存著墓主人使用痕跡的日常器物,為人們拼湊出了一幅西漢貴族活色生香的生活圖景。
清晨,辛追夫人在侍女的輕喚中起身,作為轪侯夫人,精致的妝容是她每天必不可少的一步,而案桌上的彩繪雙層九子漆奩便是她光彩照人的法寶,這是她存放個人梳妝用具和貼身物品的化妝盒,里面胭脂、篦、假發(fā)、針衣等一應俱全,尤其是一只粉撲,與如今拂在臉上的化妝工具幾無二致。侍女們圍著坐在銅鏡前的辛追夫人,有的給她擦洗梳頭,有的為她輕施粉黛,還有人給她佩戴發(fā)飾……
晨妝初罷,侍女為辛追夫人挑選穿搭,羅、綺、錦、紗、轂、素、帛、繡、綃、縞、絹……在辛追夫人的衣柜中,織物品種達十多種,其中最為驚艷的當屬那襲“云中衣”——素紗襌衣,這件西漢織造巔峰之作僅重49克,展開可覆周身,疊起能藏于方寸之間,輕透的絲縷在晨光中泛起月華般的柔暈,人們用薄如蟬翼、輕若煙霧來形容它。
《詩·鄭風·豐》曰:“衣錦衣,裳錦裳。”素紗襌衣應該是套在色彩艷麗的絲綿袍外,這或許便是辛追夫人衣柜中的另一件時尚單品——朱紅菱紋羅曲裾袍,雖歷經(jīng)2000余年時光洗禮,但其朱紅依舊明艷如新,菱紋圖案清晰靈動。經(jīng)緯交織中,纖細的絲線構(gòu)筑了一個紛繁遼闊的絲綢世界,讓人們看到了西漢初年對服飾的獨特審美,更嘆服于那個時代織造工藝的卓絕。可以想象,當辛追夫人把它套在各種華服的最外面,華服上艷麗的紋飾在這層薄紗下若隱若現(xiàn),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焦點。
待一切完成后,仆人呈上今日的菜單。辛追夫人是一位美食愛好者,她的“菜單”上記有近百道菜肴,其中肉食中除了常見的雞鴨魚豬外,還包括鹿、雁、鶴、鵝等各種野味。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轪侯家豐富的烹飪手法也遠超后人想象,羹(煮湯)、炙(燒烤)、熬(干煎)、濯(涮煮)、濡(清蒸)、昔(熏成臘肉)、膾(把鮮肉切成刺身)、脯(風干成肉脯),苦咸酸辛甘五味俱全,鼎食之家的煙火長卷有了具象化的呈現(xiàn)。
除了食材和烹制講究,轪侯家的食具也極為講究。馬王堆漢墓里出土了大量成套的漆器餐具,包括漆碗、漆盤、漆耳杯等。這些食具上書寫著“君幸食”“君幸酒”的字樣,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您吃好喝好!”雖然時光過去2000多年,但上面的字跡依然清晰,所蘊含的祝福依然真誠。
這些漆器上飾有一個常見的紋飾“云”,作為通天的媒介,云從遠古開始就給人們描摹,漢代漆器繼承了戰(zhàn)國楚文化,卷云紋和長云紋拓展出了穗狀和花卉狀的圓尾,不但造型更豐富,而且工藝更精美,漆器工藝達到了頂峰。
從以漆耳杯為代表的成套酒器來看,辛追夫人生前或許還有飲酒的習慣。在“酒為歡伯”的漢代,男女皆可飲酒,無論婚喪嫁娶、日常宴飲還是佳節(jié)聚會,酒都必不可少。酒酣耳熱之際,席間樂師奏響七弦琴,舞姬身著彩衣翩躚,楚歌鄭舞、琴瑟和鳴。此刻,辛追夫人或許正斜倚憑幾,與賓客談天說地,湘楚大地的晨昏晝夜,便在這詩酒風華中流轉(zhuǎn)輪回。
君子六藝——漢家少年的精彩人生
游人如織的展廳內(nèi),辛追夫人的遺容吸引著無數(shù)目光,但對歷史學家來說,或許展廳內(nèi)的帛書才是無盡價值的源泉。它們出土于馬王堆三號墓,也就是辛追夫人的兒子——第二代轪侯利豨的墓葬。雖然史書中沒有留下關(guān)于他的記載,但從展廳的出土文物中,我們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暫卻不失精彩的人生。
利豨墓當中總共出土了13萬多字的帛書、簡牘,均為戰(zhàn)國至漢初的文獻抄本,很多更是首次問世,如《相馬經(jīng)》——現(xiàn)存最早的相馬著作;《五星占》——現(xiàn)存最早的天文學著作;《五十二病方》——中國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最完整的古醫(yī)方專著;《長沙國南部地形圖》——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編制最準確的軍事地圖;《導引圖》——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呼吸運動圖譜……帛書內(nèi)容涉及哲學、軍事、天文、地理、醫(yī)學、藝術(shù)等領域,堪稱“漢代地下圖書館”。
可以想象,利豨從小就接受以“君子六藝”為核心的貴族教育體系,但作為轪侯爵位的繼承人,他還需通曉行軍布陣的軍事韜略,其墓葬中出土了戈、劍、弩機等大量實戰(zhàn)兵器,這關(guān)聯(lián)著長沙國的另一種狀態(tài)——戰(zhàn)爭。
今天地處內(nèi)陸的長沙,在2000多年前卻是漢帝國的邊防重鎮(zhèn),它的南面是一個和漢帝國關(guān)系時好時壞的獨立政權(quán)——南越國。透過展廳里《駐軍圖》上蜿蜒的邊境線與密集的烽燧標記,我們仿佛還能依稀感受到那段金戈鐵馬的歲月。
這幅《駐軍圖》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彩繪軍事地圖,整幅地圖上南下北,與今天地圖的方位相反。據(jù)考證,這幅圖所描繪的區(qū)域位于今天湖南九嶷山與南嶺之間。除了山脈、河流、居民點,圖上還著重標出了九支軍隊的駐地、番號、防線、行動路線等,從一些村落上標注的“某某戶今無人”“某某戶不返”等字樣,人們推測這可能是戰(zhàn)爭原因?qū)е庐數(shù)厝丝诖罅苛魇А?/p>
在《駐軍圖》旁邊則是《長沙國南部地形圖》,這幅圖繪制的范圍要更大,它與今天湖南省一大部分是重合的,即今湘江上游瀟水流域、南嶺、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區(qū),圖中水系與現(xiàn)代地圖大體相同;鄰區(qū)便是南越王趙佗轄地,約相當于今天廣東大部分和廣西小部分地區(qū)。該圖對所繪內(nèi)容的分類分級、符號設計、主區(qū)詳鄰區(qū)略等制圖原則,較為科學合理,至今仍在沿用。
和《駐軍圖》一樣,2000多年前它更為重要的是軍事用途。據(jù)《史記·南越列傳》記載,呂后臨朝五年(公元前183年),南越王趙佗“發(fā)兵攻長沙邊邑,敗數(shù)縣而去焉。”兩年后漢廷中央派兵出征南越國,人們推測,十幾歲的利豨作為長沙國軍事統(tǒng)帥,很可能親率部隊參與了這場戰(zhàn)爭,長沙國南部的深山密林潮濕又酷熱,很多士卒們都染上疾病,戰(zhàn)況異常艱難,前后持續(xù)了約一年多的時間,直至呂后駕崩(公元前180年)方告結(jié)束,這兩幅圖很可能就是利豨在南方駐軍布防時留下的。
史書對這場征戰(zhàn)的記載極為簡單,但通過展廳內(nèi)的一幅帛畫——《車馬儀仗圖》,我們可以一睹漢家少年利豨校閱三軍的英姿。畫中的右上方是車騎方陣,右下方是騎兵方陣,左下方正有人鳴金擊鼓,左上方有一隊侍從簇擁著頭戴高冠、腰佩長劍的利豨走向前去。這很可能就是利豨檢閱軍隊的情景,據(jù)《史記》記載,第二代轪侯利豨“年十八嗣位,掌長沙國軍務”,整幅畫以他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來,少年將軍的雄心如同漢帝國的昂揚之勢,這恢宏的場景定格了利豨在一生最 耀眼的時刻,只可惜天不假年,就在少年英雄熱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時,卻不幸英年早逝。
T形帛畫——羽化登仙的永生之夢
在兒子利豨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也溘然長逝。在西漢黃老思潮浸透的時空里,死亡并不可怕,而是“歸根復命”的起點。人們把對死后世界的極致渴望和浪漫想象,通過墓葬藝術(shù)的形式來展現(xiàn),因此,墓穴既是死者的地下家園,也是靈魂幻化的場所。
辛追夫人的墓葬規(guī)制采用“一槨四棺”的五重結(jié)構(gòu),這與她諸侯級別的身份相符合。最里層棺名叫錦飾漆棺,這是直接裝殮辛追夫人遺體的內(nèi)棺,在蓋板和四壁板上飾有多種顏色的羽毛,這便是傳說里的“羽衣棺”,所謂“羽化而登仙”,在中國考古發(fā)掘史中尚屬首次發(fā)現(xiàn)。
錦飾漆棺的棺蓋上平攤著一幅呈T形的彩繪帛畫,由三塊單層細絹拼成,名叫“非衣”(即“飛衣”),這是墓主靈魂升天的媒介,是古代的一種招魂幡,出殯時引作前導、入葬時覆蓋在內(nèi)棺上的“銘旌”。
T形帛畫自下而上可分為三重空間,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與重生之地,被靈蛇環(huán)繞的力士腳踩兩條鯨鯢托舉著平臺,這象征著大地,平臺之下,即古人所說的水府(黃泉)。大魚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同時也構(gòu)成了陰與陽,生與死的界限;向上為第二個空間即人間,畫面中擺放著各種器具和食物,這是家人們正在為辛追夫人舉行祭祀儀式;繼續(xù)向上,以玉璧為中心,兩條巨龍穿璧而過,似乎在引導墓主人之魂升天,璧上立一斜柱,其上一平臺,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侖的傾宮和懸圃。平臺之上拄杖而立的婦人正是辛追夫人靈魂的化身,她在婢女的服侍和天國使者的迎接下準備升天,再往上,兩根立柱構(gòu)成一道關(guān)隘,或許就是傳說中的天界,頂端正中間坐著人身蛇尾的燭龍,其左側(cè)掛有一輪彎月,月上繪有蟾蜍、玉兔,月下有一位托月女神,天界環(huán)繞著仙鶴、飛龍、司閽(天國守門神)等一眾仙獸,還有九只金烏,昭示著辛追夫人的靈魂已經(jīng)到了天界。
帛畫設計的空間與圖像組合,描繪了通向天國的儀式與途徑,體現(xiàn)了漢代的宇宙觀和生命觀,雖然關(guān)于每個圖案蘊藏的含義眾說紛紜,但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圖案在整體上敘述了從“死”到“永生”的流程。
錦飾漆棺外面是朱地彩繪漆棺,這是色彩最艷麗、構(gòu)圖最繁雜的漆棺,帶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侖位于這一重棺的中心。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西經(jīng)》中,昆侖山被稱為“帝之下都”,是傳說中離天最近的地方,那里有不死靈藥,凡人借此可登入天界。
朱地彩繪漆棺外面為黑地彩繪漆棺,造型優(yōu)美的卷云紋,像是在流動穿梭一樣,構(gòu)成一個奇幻的天界景象,暗喻著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氣”。《莊子·知北游》寫著:“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漢代墓葬里有大量的云氣紋,目的就是為了聚氣永生。黑地彩繪棺上繪有神獸、神怪、仙人、鸞鳥、鶴、豹,以及牛、鹿、蛇等十多種形象,栩栩如生的神怪肩負著重要的任務,保護黑暗世界中的辛追夫人,這也代表著辛追夫人由“帝之下都”昆侖上升九天。
最外面為黑漆素棺,全無紋飾,隨著棺蓋的合攏,留給外人的只有單調(diào)而又莊嚴的玄色,這代表著“包裹天地”“玄之又玄”的“道”。象征著辛追夫人“得道升天,魂歸大道”,是道家思想的精髓。2000多年后,當人們看到辛追夫人宛如夢中的千年遺容,留給世人的不僅僅是驚鴻一瞥的驚艷,這種超越時空的完整存續(xù),恰如《禮記·郊特牲》“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理念的物質(zhì)化詮釋,這也正是漢帝國對生死的浪漫注解。